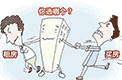在國際足聯的官方網站上,參加女足世界杯的運動員,都有一欄注明她們所效力的俱樂部或者大學隊。也有一些人這一欄空缺,這意味著,踢球現在並不是她們的“主業”。
加拿大隊中就有六七名這樣的隊員,比如艾米麗和塞萊尼亞,如果不是為了踢世界杯,兩人眼下應該正在溫哥華的某個街頭,開著自己的流動卡車販賣甜品。
她們倆從少年隊一直踢到加拿大國青隊,友誼延續了十幾年。訓練和比賽之外的時間,也想干點別的營生。2012年,兩人在美國俄勒岡州沖浪時,遇到了一輛販賣食品的流動卡車,受到啟發,於是開始踢球之外的“練攤”生涯。
踢球、謀生、學習,在很多女足運動員的生活中,這是幾項並行不悖的內容。2012年,加拿大女足奪得倫敦奧運會銅牌,聲譽達到頂點。但一回國,前鋒梅麗莎就趕回學校去完成學業,“總得要一項踢球之外的技能,今后也能有所依傍。”
美國女足聯賽運作已經相當成功,在聯盟中,一名球員的年薪從6000到4萬美元——也就是說,一些球員的工資要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。這是一個讓人有些驚訝的事實,但也是眼下女足運動職業化的現狀。
實際上,不管艾米麗、塞萊尼亞還是梅麗莎,在聽到國家隊征召的消息時,都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加入。理由很簡單,熱愛與快樂。踢球是她們從少年時代就追逐的夢想,生活需要繼續,而踢球則是更高層面的滿足,並不矛盾。
多年來,國內女足的清苦似乎已經為這項運動貼上了標簽。也有過女足選手“練攤”或者開網店的消息,都是為了佐証女足的不易。但是,對這項運動的熱愛,其實無分國界,也不因收入的多少而有所改變。所不同的是,踢球的加拿大女孩始終明白“踢球不是生活的全部”,而踢球的中國女孩,要為之付出更多。
正因為生存的土壤不同,也催生了看待問題的不同角度和方式。在加拿大,女足運動廣泛流行於校園,再喜歡踢球的女孩也不會放棄學業。至於今后是踢球還是干別的,更多是一種個人選擇。在國內,一個女孩子能踢到省隊已經很難,更難的是如果接著踢下去,未來的選擇會越來越窄。不是說女足運動員就該甘於清苦,而是這項本該屬於草根大眾參與的運動變成了幾千人從事的“小眾運動”,在封閉的體系內循環,又何談拓展的空間和應有的回報。世界杯賽場上,年輕的中國女足表現出了重回一流的強烈沖勁。而要從深層次改變女足運動的境地,還得從社會化的根基做起。

 分享到人人
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
分享到QQ空間










 恭喜你,發表成功!
恭喜你,發表成功!

 !
!